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李伯重教授访谈录

环球交叉点
看看新闻Knews综合
2024-06-17 10:47:32
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即将于6月20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来自中欧近60名专家将围绕“中国学与欧洲的中国观”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日前,中国经济史研究权威学者、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先生在上海就这一话题接受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武研究员的专访。

李伯重
周武:李先生好,感谢您接受邀请,参加即将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学和欧洲的中国观”。您过去常赴欧洲讲学,并长期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是该学会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执委会委员,跟欧洲学术界有过不少交往、合作,对欧洲中国学研究现状比较了解,在您的印象中,欧洲中国学关注的热点或议题有哪些?
李伯重:感谢中国学所邀请我参加本次访谈,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真心希望中国学者和欧洲学者能够加深了解,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敞开思想,真正知道对方怎么想,这对学术有益,也对双方人民有利。
我对欧洲中国学略有了解。其中,法国和荷兰的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都有重大进展。在法国就是年鉴学派的兴起。年鉴学派兴起之后,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有评论说:“这是一次法兰西史学革命”。
这个革命,对世界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年鉴学派做的研究在西方世界我觉得是独树一帜,而且影响很大。在年鉴学派掀起的新史学潮流中,法国的中国史研究也从年鉴学派发展起来,出现了新的观念、新的方法。在这方面,法兰西学院教授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先生是一个代表,他应该是目前在世的法国汉学家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位。他最出名的著作《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已经在西方成为经典。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
荷兰学者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他们用历史国民账户系统进行研究,把各个部门的经济状况用数据结合起来,得出比较完善和更为全面的认识。在2000年瑞典的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扬.路易腾·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 教授他的启发下,我也开始学习历史国民账户系统的研究方法,之后用此方法,花10年时间写了《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一书,并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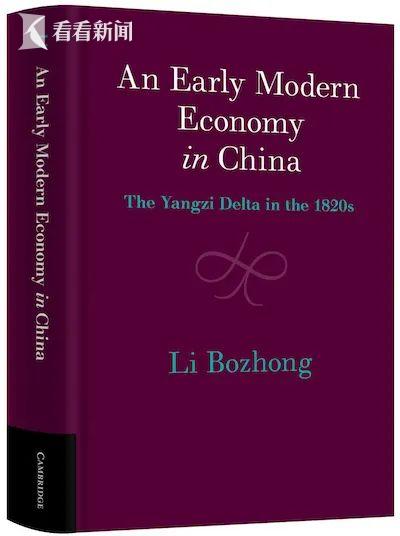
《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英文版
我觉得双向交流对彼此都有很大促进。从我个人来说,我从欧洲学者那里学到很多,并用学习到的方法做中国史研究,这样可以使他们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如果没有双向交流,我做的研究不可能进行;从一些欧洲同行来说,如果我们没有用他们来讲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很可能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是双向交流对话,是学术方面的重要举动,我觉得非常重要。
周武:2002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时,采访过孔飞力教授,跟他聊到法国汉学。他那时正好出版了他应邀在法国发表的专题系列讲座讲稿英文版,也就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我问孔教授:“您感觉欧洲汉学,跟美国中国学对比,两者各自特色是什么?”他说:“别看现在法国做中国研究的,欧洲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好像没有美国多,但他们的学术水准依然是世界最高的”。他的看法正好呼应您刚才的看法。从您自身的学术实践,特别是跨国学术交往的经验出发,您认为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要特别注重哪些方面问题?
李伯重:欧美学者过去在理论、观点和方法上有不少创新,但一些学者过分注重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但实证研究有时会稍差一些。前面说的法国学者,他们在实证研究方面的努力,我觉得许多美国学者有诸多不如。从世界中国学的长远发展来说,理论和实证都要加以重视,不能偏废。
我们鼓励创新,但要避免把那些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拿来硬套中国历史。对于各种理论和方法,我们应该择优而用,好的采用,不好的应避免。深入的中西交流,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周武:您刚才讲中外之间的学术交流非常重要。我们既要认识到别人的长处,也不能一味用仰视的姿态。交流是平等的,但平等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就是自己要有东西才能够跟人家平等对话。如果自己做得不够好,就没办法跟人家对话,也没办法赢得尊重。
您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从研究生时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是中国学界深度参与江南研究国际对话的一个重要代表,多部著作被译为英文出版,数十篇相关论文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长期以来,江南研究,当然也包括上海研究,一直是世界中国学领域中最为活跃的一个论域,堪称国际性显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学术界有关中西历史“大分流”大讨论的持续演进,江南研究更因此而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您不仅关注,而且躬身入局,全程参与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有的学者干脆把您视为加州学派的一个核心成员。您一直倡导从全球经济史视野研究江南,特别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为什么?您认为什么样的比较研究才是比较科学的?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李伯重:我分几个方面来讲,首先,江南这个地区确实是太重要了,不是因为是我们生活的地区,所以我们自己觉得重要,其实在学术上,每个地区都重要。但江南有它的特殊性。我做研究生时,傅衣凌老师指导我写博士论文,要我先去查阅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设的东洋学文献中心编辑《东洋学文献类目》(前身为《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了解一下国际学坛中关于明清江南史研究的情况。
我看了之后,发现在这个收集了中、日、英、法、俄五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目录中,在关于明清中国史的成果中,大概1/3的文章是讲江南的,另外1/3是讲全国的,但是都提到江南,而研究中国其它地区的只占1/3。由此可见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和在中国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当然,研究的人那么多,研究的难度就会更大。因此,要做出一些前人还不曾做出来的一些成果,就必须采取新方法。
中国过去对西方的看法,我觉对大多数人来说,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歪曲的西方。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歪曲的中国。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江南。早期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首先是到江南。他们觉得江南这个地方很富裕,人民都很讲秩序,士大夫彬彬有礼,儒家的礼教很深入。所以他们把这个印象带到了欧洲。但随着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入,发现江南与其它地方差别实在太大。同样,中国过去认为欧洲先进,中国落后,看到的就是英国、法国少数几个国家,实际上欧洲也有不少落后和贫穷地区。中国和欧洲都是一个很大的地区,里面各种各样的地方文化,差别非常明显,如果要做比较研究,只能选取可比性比较高的地区来进行。
在欧洲各个地区之中和江南最相似的,我觉得就是荷兰。江南的面积和荷兰差不多;这两个地区分别位于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在亚洲东部,一个在欧洲西部,分别在欧洲和亚洲两条最大的河流长江和莱茵河的河口;两个地区都很低洼,河网密集,交通方便。从17世纪开始,荷兰人是欧洲最勤奋、节俭的人,江南的人也非常勤奋节约。这些都是有很多共性的地方。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两个地区至少在17-19世纪初期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荷兰的人均GDP比英国还高,直到1800年左右,荷兰的技术在各个方面都要领先欧洲。而江南在亚洲也是如此。但这两个地区到了19世纪,命运又发生变化,都被它们旁边的两个岛国超越,这也是很有趣的。因此通过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更好的认识对方,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19世纪的上海
自我认识非常重要。过去江南一直被认为“富甲天下”,但到了20世纪出现了相反情况,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过去一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江南也不例外。但如果阅读欧洲方面的记载来看,那又得出完全相反的印象。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船到了上海,一个叫胡夏米的人上岸一看,老百姓吃的很好,身体都很健康,食品很丰富又便宜。鸦片战争后两年,法国商务代表团来到苏州,一位叫做耶德的成员说苏州是世界上最大、最美、最富的城市,他用若干的赞美词来描写他所见的苏州。
那么到底江南是穷是富,就必须做一个比较。我和前面谈到的那位荷兰经济史学家范·赞登用购买力评价作为标准,对这个两个地区各种物品的价格进行计算,然后来评估这两边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发现江南生活水准绝对不差,特别松江这个地方。
在1820年左右,江南人均可以到1000美元左右,荷兰比中国要高,大概在1800美元左右,而那时西欧(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平均水平也就1100美元左右。所以,江南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富的地区,但绝对是富裕地区之一。
这说明,中国过去并不是很差,特别是江南。江南发展有自己的内在动力,所以它能够达到很繁荣的水平。所以必须通过比较科学的量化比较,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背后的真实。2000多年前墨子就说得很清楚,他说“异类不比”,不是同类的东西不能相比,然后说“说在量”,就是比较必须衡量,只有这样比较才有意义。我觉得通过两个地区的比较研究,不仅让我们更好认识欧洲,也更好认识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客观定位。

周武:您有一本有关理论方法的书籍——也就是《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这本书的“趋势篇”里特别强调,中国的学术发展要融入世界。华东师大哲学系著名哲学史家冯契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提出一个看法,他认为现在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是“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国学术真正要在国际上赢得尊重,要赢得话语权,就要参与到这个“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当中去,在同一个平台上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交流互鉴。请您谈谈,现在中国的学术发展要如何更好融入世界学术体系并获得更大的学术话语权?
李伯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般而言,科学无国界,因为它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列宁说,一个人如果不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列宁说必须学习、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不是说只是某一方面的知识。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的国际学术规范和话语体系是从欧洲起源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欧洲产生的。现在的国际学术体系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的体系。如果不进入这个国际学术体系,那么我们的研究成果别人就很难了解,成为自说自话,很难与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交流。只有进入这个体系,在其中进行学术创新,才能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这和我国加入WTO类似。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没用太长时间就成长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既不能排斥,也不能盲从。一方面要承认它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要对不合理之处进行改进。我们对国际学术体系中的不合理之处所作改进的越多,我们的话语权也就越大。因此,我们要积极进行学术开放,而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与国际学术相隔绝的学术孤岛。我们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时也从别人那里学习到更多东西。
| 编辑: | 应鋐 |
| 责编: | 张悦 |
版权声明:本文系看看新闻Knews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暂无列表

全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