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审公廨”到“特区法院”——浅谈近代上海租界法权的变迁

旧时光里的上海滩
邱力立
2019-05-10 13:42
“会审公廨”又称“会审公堂”,是在近代上海租界内长期存在的一种为审理和裁判华人或华洋之间诉讼而设立的特殊机构,其在影响中国近代司法制度的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法权沦丧的典型事例之一。

会审公廨旧照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均成立于1869年,在这之前,上海租界内对于华人或华洋之间的诉讼大致经历有如下这四个阶段。
1、1843-1853年,在这一时期中租界内“华洋杂居”的局面尚未形成,相关诉讼以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订立《上海土地章程》第十二款中“如有在此界内赌博、酗酒、匪徒滋事、扰害商人者,由领事官照会地方官照例办理,以示惩儆”为处理准则,即除了具有“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有时也被称为“治外法权”,指当一国公民在侨居国成为民事、刑事诉讼的被告时,该国领事具有按照本国法律予以审判、定罪的权力)的国民作为被告的诉讼外,其余均移送上海地方政府处理,上海地方官也有权向租界内传提相关“人犯”。
2、1853-1856年,在这一时期中受“小刀会起义”的影响(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内逐步开启了“华洋杂居”的局面,相关诉讼数量较之前十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加之此时上海地方官因战事也无暇顾及到“租界内的华洋之事”,于是租界内英美法三国领事便借机“担负”起了对于租界内“华人或华洋之间诉讼”处理者的角色,其中除了案情较为严重者仍需移送上海地方政府处理外,其余均由领事们“自行处理”。
3、1856-1863年,上海地方政府在经历之前的战事后对于发生在租界内的“华人或华洋之间诉讼”试图恢复到1853年之前的管理状态,但同时租界内的领事们也不愿因此而轻易放弃于1853-1856年间所“获取到的既有权益”,因此上海地方官至租界内传提“人犯”开始出现了一些困难,如1862年上海道与美领署订立美租界章程中就有规定“有拘票者,必须由美领事签字方可在租界内拘捕”,由此外人开始对于发生在租界内的“华人或华洋之间诉讼”有了一定管辖权。
4、1863-1869年,随着太平军东征后租界内华人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外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开始计划在租界内成立一个可以管理华人的司法机构,对于该机构是否应由外人直接主持,时英国领事巴夏礼认为“在租界内设立一个置于外国人控制或管理之下的完全独立于中国法院系统的审判机构也是对于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由此该机构在成立前最终被设定为“由中国官员”主持,上海道委派一名官员至租界英国领事馆内与副领事会同审理有关诉讼,1864年5月1日该机构正式成立,称“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我们一般可以把它看作是后来“会审公廨”的前身。

巴夏礼

原位于外滩的“巴夏礼铜像”
“会审公廨”的出现是在1869年,依照当时由中外双方共同议定的《洋径浜设官会审章程》而成立,成立前法国领事因该章程中的部分内容“与法方习惯不合”而退出,故而才有了之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两个不同的“会审公廨”。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主要依上述《洋径浜设官会审章程》来作为其日常审理的基本准则,上海道委派一谳员(一般为“同知”官衔)至租界内在领事馆官员的“协助”下进行案件审理,其管辖范围一般为“华人或华洋之间“的民刑事诉讼(具有“领事裁判权”的国民作为被告的除外),如遇军流徒以上罪状或人命案仍归上海地方政府审理;在具体审理形式上“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在成立初期一般表现为”华主洋辅“,即在审理纯粹由华人之间引发的诉讼时全凭”华官“主持领事馆官员不予干涉,只有牵涉到洋人的诉讼时,领事馆官员才会以”会审“、”陪审“、”听讼“等不同形式加入到诉讼的审理中(据姚远所著《上海租界与租界法权》一书59页中梳理介绍:如果案件涉及“有约国”外人,谳员须与该国领事官或他所派出的官员共同审理“会审”。如“无约国”外人诉讼,该谳员可“自行审判”,但须邀一名外国官员“陪审”。审判中给外人酌拟的罪名,应该报上海道等上级官员检查,并与一名领事“公商酌办”。如果是外人雇佣、延请的华人涉讼,领事官或其所派的官员可到场“听讼”);另外因”会审公廨“适用西方的律师辩护制度,因此在公廨审理过程中,华人也可以聘请律师为其出庭辩护。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曾先后设于南京路香粉弄及现“上海第一食品公司“等处,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后移至现浙江北路近七浦路处,现浙江北路191号内还能看到原“会审公廨”及后来“上海特区法院”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建筑。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旧照

浙江北路原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旧址
“法租界会审公廨“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相比对于中国法权的侵犯更大,如在“法租界会审公廨”中无论“华人还是华洋之间的诉讼”均由上海道委派的谳员与领事馆官员会同审理,公廨的诸多事务中方谳员无权过问,公廨提传法租界内华人的签票都须经过法国驻沪领事签字等。另“法租界会审公廨”在聘请律师上也是多有限制,只有在达到一定“标准”以上的诉讼中才能聘请律师且律师必须是法国籍,由此也带动了一批当时沪上法籍律师的迅速致富,现太原路160号太原宾馆的原住户、素有“强盗律师”之称的狄百克就是这些法籍律师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太原路160号花园住宅

法籍律师狄百克
“法租界会审公廨”初设在位于公馆马路(现金陵东路)的法国领事馆内,后于20世纪10年代中期改为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隶属的一个机构并在不久后迁至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现在建国中路20号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内内还能看到当时法租界警务处和会审公廨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建筑。法租界会审公廨大楼是由一位名为“望志(Wants)”的建筑师所设计的,据蒋杰所著《法租界会审公廨、警务处与薛华立路的开发(1900-1939)》一文中的介绍:“在1914年7月9日工务处例会上,市政工程师、建筑学家望志被任命为薛华立路工程的负责人。他被要求在1915年9月15日前,为建造新楼做好一切预备工作。经过多次论证论证,在1914年11月13日,工程处终于通过在薛华立路新建大楼的计划…1915年9月17日,(法租界)会审公廨大楼正式竣工,并通过公董局工程处的验收。新落成的大楼由地下室和两层楼房构成。在地下室设有洗澡间和卫生间,第一层设有法庭和审议厅,第二层设有8间办公室,供会审公廨的工作人员办工…大楼建成不久,便传来不幸消息。负责工程设计的望志工程师在工程竣工一个月后因伤寒逝世了。这位杰出的工程师为法租界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作品,如市政花园(le Jardin publique)和法国总会(Cercle sportif),会审公廨大楼是他留给上海法租界的最后一个作品。为表彰望志为法租界城市建设做出的贡献,公董局决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新建的马路,即后来著名的望志路”,这条望志路也就是现在身处“新天地”中的“兴业路”。

法租界会审公廨旧照

建国中路原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
“会审公廨”自成立后逐步被英美法等列强国家的驻沪领事馆、租界工部局及公董局等机构所把持,其审判权限也被进一步扩大(据姚远所著《上海租界与租界法权》一书60页中介绍:通过多次的交涉,会审公廨扩大了审判权限,获得判处五年以下徒刑的权力,而在事实审判上甚至擅自判处无期徒刑…),华人也越发对其产生厌恶情绪,发生在1905年的“大闹会审公堂案”是20世纪初华洋在“会审公廨”问题上矛盾激化的一次典型事件,该事件因工部局捕房以“拐骗人口罪”拘捕某中国官员遗孀黎黄氏(也有说法称为“黎王氏”或“李王氏”)而起,后在会审公廨的审理中“英国陪审员”、英国驻沪副领事德为门(B.Twyman)因不满中国谳员关炯之(关綗之)对此案的处理从而导致双方由言语争执演变为肢体冲突,在德为门强令巡捕房带走黎黄氏的过程中有多名中国廨役被打伤,此事后在上海引发轩然大波并且还惊动了北京公使团及清政府的外务部…列强对于会审公廨试图控制的欲望由此可见一斑。

会审公廨旧照

关綗之
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驻沪领事团在清政府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乘乱非法接管了上海两大会审公廨,其审判权限被空前扩大,同样据姚远所著《上海租界与租界法权》一书60页中介绍:“在此(辛亥革命)期间,这两个会审公廨有权审判任何案件,甚至死刑案件。而华人放入民事案件也须洋人陪审,公廨判决,并不得上诉”,至此“会审公廨”已俨然成为了一个存在于中国国土上的外国法院。
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从1912到1930年的这18年中客观上讲北洋政府、上海总商会、上海律师公会、南京国民政府等均为“收回会审公廨“作出过一定的努力,这18年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界,前13年中方在“收回会审公廨”的道路上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正所谓“弱国无外交”,“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清王朝腐朽的统治,但却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尤其是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国内进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更是在对于“收回会审公廨”的问题上“有其心而无其力”。赵晋卿是“收回会审公廨”的亲历者与主要参与人之一,他在《收回会审公廨交涉的经过》一文就有写到中华民国前期中国政府在对外试图收回会审公廨时的艰难,其在文中写到“中国在(1919年巴黎和会)会上提出收回治外法权问题,各国以此种问题不应在此会议上讨论为理由拒议…在(1921年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上,王宠惠就收回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发表长篇演说,并说明中国正在进行拟定完备之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商法之工作,(从全体大会通过的决议来看)各国在原则上似乎同意我国收回治外法权,但却附列若干苛刻条件。我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收回法权,仍无实际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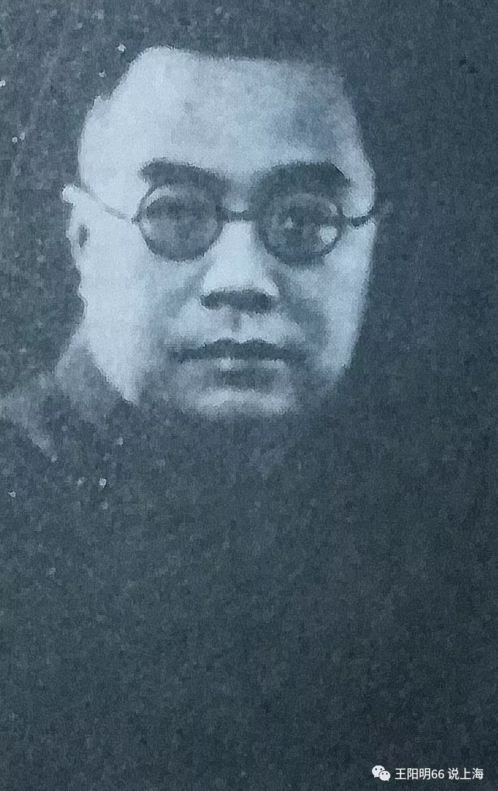
赵晋卿

王宠惠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大大加快了“收回会审公廨”的进程,当时的华人各阶层虽然在参与这次运动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导向(如:中华民国政府当局希望借此运动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华人资本家希望借此运动来为自己进入工部局董事会加大砝码、而工人大众则希望通过参加运动来减轻外国资本家对于自身的剥削…),但正是这样一次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团结”却在事后着实对于租界当局的“傲慢”给予了有力的回击,“收回会审公廨”从“五卅运动”起已是“箭在弦上”。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外交部与驻京外国公使团”的首回合艰难谈判交涉下,至1926年4月底,会审公廨先是基本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但列强们对于“收回会审公廨”的具体时间却依旧没能给出任何明确答复。
针对驻京外国公使团的“强悍”及谈判有可能会陷入到的僵局,从1926年4月起北洋政府当局开始有策略性的将“收回会审公廨”的谈判双方由“中华民国外交部与驻京外国公使团”转变为“江苏地方当局与驻沪外国领事团”,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律师公会的代表们至此正式加入到“收回会审公廨”的“中方谈判团队”之中,时又正巧地方军阀实力派孙传芳“坐镇江苏”正在筹划淞沪商埠办公署并“颇思有所作为,以得上海民心之拥护”,故而“收回会审公廨”一事在转到地方“就地协商”后也并未遇到丝毫耽搁,就在“五卅运动”近一周年后的1926年5月4日,淞沪商埠办公署成立,公署总办丁文江与外交部特派员江苏交涉员许沅在上海总商会、律师公会等组织的协助下开始向“收回会审公廨”的目标发起冲击,谈判初定的四项目标为:1、民事案件全部收回,2、刑事会审权收回,3、领袖领事对于传票拘票的签字权收回,4、检察权收回,时中方外交部参事厅对此安排表示“收回会审公廨由沪就地办理,极为妥善”。
虽然中方自“五卅运动”后在“收回会审公廨”一事上屡次“主动出击”并积极调整应对策略,但“长期盘踞在上海”的列强势力显然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拱手交出“特权”,如在上述“中方四项目标”的谈判中,最后对于中方来说有实质性进展的也仅有“民事案件”及“领袖领事传拘单签字权”这两项,其余多以中方作出让步而收场。另外久居沪上的外国律师团体也是这场“收回会审公廨”谈判的密切关注者之一,当他们得知会审公廨的收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上海的“生计”时,外籍律师团体的不满情绪开始了总爆发,各种不满的宣泄开始频繁出现在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端,其中有宣称“中国无国宪、无法典、无已成之法规,问官判案,随一人之好恶及高官、大吏、公所团体、亲戚朋友之势力而已”(见1926年7月21日《申报》之《公廨案之各方消息》),也有认为“江苏省政府实际上不过是孙传芳上将之军阀政府…上海领事团从北京政府手中获得会审公廨的权利,当然仍返之北京政府,孙并非合适的谈判对手”(见1926年7月17日《申报》之《公廨案昨日继续会议》)…“收回会审公廨”就是在这样“强敌林立”的艰难曲折中一天又一天的进行下来的,中外双方在针对所谈判问题一一折中后于1926年9月27日正式向社会公布《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以下简称《暂行章程》),将原本的会审公廨(仅指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并未在此次谈判中收回)改为临时法院并定于1927年1月1日在当时上海北浙江路(现浙江北路191号)的会审公廨进行交接仪式,从此会审公廨在上海的历史基本接近尾声。
当然,会审公廨的收回并不意味着外国势力就此退出了上海的司法舞台,正如当时在收回会审公廨谈判期间孙传芳曾认为的那样“完整彻底的收回会审公廨事实上骤难办到”,因此即便已经没有了会审公廨,但这个新生的并且还带有些先天不足的“上海临时法院”在很多领域其实依旧承受着外人的掣肘,曾担任过“上海临时法院”院长的何世桢曾为此专门写过一篇《记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的回忆文章,我们从这篇文章中就能清晰的看到当时的临时法院究竟是一副何等模样,此文中写到“临时法院只有签发各种司法命令之权,其执行权仍然操在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工部局手里。对刑事案件、侦查和起诉权也操在工部局手里…法院内部的人事权虽说归江苏省政府自主,但书记官长却必须用外国人。这个职位,相当于一般机关的主任秘书或秘书长,具有机关行政的统率、指挥之权,虽说听命于院长,但实际上凭借领事团和工部局的背景,院长有时也不能不按照他的意见行事。更有一件气人的事,就是会审公廨虽然取消了,但各国驻沪领事还保留了会审和观审两项权利。根据协定,凡原告是外国人,或是所审理案件对租界治安有重大影响者,有关领事都要参加会审。至于观审则并无限制,只要领事老爷高兴,随时都可以参加。名义上,观审者对审理案件无发言权,但他们对重大案件,总是要以自己的影响来左右法院,从来不甘于作壁上观…”。

何世桢
除了何世桢所叙述的这些之外,《暂行章程》也没有对外籍律师作出明确的限制,当时临时法院的“法警”与“监狱”都与工部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临时法院的法警由工部局警务处选派(依《暂行章程》第四条),监狱仍基本被工部局警务处掌控(《暂行章程》第三条:凡附属临时法庭之监狱,除民事拘留所及女监当另行规定外,应责成工部局警务处派员专管)等。在案件的属地管辖范围上“临时法院”相较“会审公廨”时期有所扩展,其不仅包含租界内几乎所有的民刑事案件(涉及到领事裁判权的除外),而且发生在黄浦港、上海宝山两县的华洋民刑事案件也归“临时法院审理“。”临时法院“所适用的法律一直以来也是它被诟病的另一个焦点,因”临时法院“在审判中会参考”会审公廨“时期的法律法规,而会审公廨时期的法律法规又部分会涉及到《大清律例》,因此也就出现了在中华民国的历史时期中却还在参考着本已被”淘汰“的《大清律例》的奇怪现象,由此可见在当时”收回会审公廨“虽然已是民心所向,但从客观上来讲设立”上海临时法院“的进程还是显得比较仓促的,有很多原本需要认真准备的事宜在”临时法院“设立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缜密的思考与落实,因此”会审公廨“虽已收回,但我们也只能把”临时法院“看成为是一个在近代上海租界法权收回过程中的”过渡性机构“,它所欠缺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太多。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依据《暂行章程》中“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有效期至1929年12月31日“这一规定及之前在对于“收回法租界会审公廨”等事宜上所遗留下的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向各国公使再一次发起了”进一步收回法权“的谈判,谈判过程同样费尽周折,由于当时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弱国”的地位依旧没有改变,故而该轮谈判在争取到较多权益的同时在部分问题上依然以中方的妥协而收场,诸如领事裁判权之类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意义上的解决。最终在1930-1931年期间,取代”上海临时法院“的”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后更名为”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第二审上诉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取代”法租界会审公廨“的”法租界特区地方法院“(后更名为”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第二审上诉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先后改组成立,至此国人在对于租界法权艰难收回的道路上也算是跨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

浙江北路原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旧址
对比“特区法院”(主要指“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与“临时法院”的区别,其主要进步的领域有如下几点:
1、外国领事的会审观审权被收回,从此中国法官可以进行独立的审判;
2、在“临时法院”时期由外国人掌控的“书记官长”这个重要职位的任免收归“法院院长”;
3、在“临时法院”时期由工部局警务处选派的“法警”虽仍由工部局推荐但推荐对象则“应可行程度应推荐中国人”,且这些“法警”在着装上须穿中国法警制服及须服从法院的命令,高等分院院长对其有任免的权利;
4、设置检查官以制衡“法警”之权(但在实际执行中该职位受谈判协定影响发挥作用不大);
5、在适用法律上均按照当时中国的法律,进一步贴近当时中国的司法系统;
6、对外籍律师的出庭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并非所有案件外籍律师都能出庭且出庭的外籍律师须服从当时中国的法律法规。
在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上“特区法院”虽然依旧没能摆脱过去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掣肘,但在客观上由于受“一战”之后国际环境改变等事件的影响,当时在中国受“领事裁判权”之利的国家数量也在降低,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有德国、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墨西哥五国先后被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至于其他列强国家在中国领事裁判权真正意义上的废除那还要等到40年代中叶“二战”结束后,我们本文的叙述也在此先告一个段落。

浙江北路原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旧址的大门
集笔者“数年走访收集总结之精华”的新书《觅.境——旧时光里的上海滩》已在2018年十月与广大读者见面,大家如感兴趣可以关注,谢谢!
—END—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王阳明66 说上海”
暂无列表
